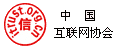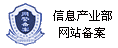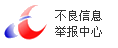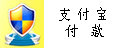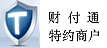政治哲学视野中的“日常生活审美化”
对于一贯喜欢望文生义的中国学人来说,对于“日常生活审美化”进行的探讨,人们想当然地把它当成是一个审美和美学(包括文艺学)问题。把“日常生活审美化”和美学困境联系起来,这当然也算是一个敏锐的观察,但呈现在这样的“审美”凝视的目光中的,也只是“审美”的某种平面上扩展和“增量”。就“日常生活审美化”成功地虏获了它的赞美者,使他们再也看不到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视野之外的任何东西这一点来说,它确实是一个问题,或者说,在更大的范围内,正是“日常生活审美化”本身的意识形态效应和问题症候之所在。按照施特劳斯的看法,政治哲学涉及的是关于“完美政治”的问题,而后者又指的是一个有目的的社会生活的整体而非后者的局部性的派生物[1],所以,既然“日常生活审美化”不可避免地关系到整体性的“日常生活”和“人应该如何生活”这样的政治哲学的核心关怀,那么它在更大程度和更基本的层次上,涉及到的是政治哲学问题,至少与之产生大幅度的问题交集。实际上,就中国当下的历史条件而言,“日常生活审美化”正是作为政治哲学思维和政治哲学问题的某种症候出现的,因此,从政治哲学视野出发,就不是观照“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诸多“视域”和“范式”之一,而是其绝对的对立面,这就使这种观照带有了终极性和包容性。
一、作为政治哲学问题症候的“日常生活审美化”
在没有任何的伦理规定、文化理想和政治目标的情况下,一个国家和文明共同体就会只剩下纯粹的经济契约、经济关系和经济网络,以及它们之间的自给自足和内部循环的自律性——从某方面的观点看来,这个上帝般全知全能的经济世界已经够了,它通过“市场”和经济手段就可以解决人类生活的一切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日常生活审美化”不是对于康德以来的经典美学的终结和颠覆,而是康德美学自身逻辑的片面伸展和极端性表现。它是康德的先验哲学所表征的经济自由主义逻辑的一种大幅度的量的扩张,同时也是对于自由主义的终极性论证;它不仅仅停留在私人生活和人的感性领域,而且也要全面地占领一些人臆想中的“公共领域”,从而整体上是对于某种生活伦理和生活组织方式的含混的表述和迷离的赞美。一些对于过往年代的记忆苦大仇深的人,看到这样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所带来的消解性和解构性力量而兴奋不已是可以理解的,不过这样的兴奋不应该淹没我们的理智和对于当下文化现实的真实感。“日常生活审美化”并不像人们所乐观地估计的那样,是一种感性的全面解放,至少,它在一方面是解放和释放的同时,另一方面也同样是对于感性深层次的压抑和体制化——再次的体制化和再次组织。由此它也并不只是一个艺术和审美问题,因为它同样使得艺术和审美成了问题,面临根本性的困境和危机: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个审美化的普遍过程,仅仅是以审美手段把精神生活的其他领域也私人化。当精神领域的等级体制瓦解时,一切都变成了精神生活的中心。然而,当审美被绝对化并被提升到顶点时,包括艺术在内的一切精神事物,其性质也发生了变化,成了虚假的东西。[2]
施米特在上世纪20年代的论述,在今天的中国问题上看起来是那样地切中要害,这反过来恰恰为我们当下的历史情境和历史条件作出了精确的定位。审美从来不是像它看起来、尤其是以“审美”式的眼光看起来那样,只是一个超脱的、纯粹的形式关系,美本身也从来不只是一种形式化的东西,甚至一种“形式的形式”(席勒),它从来都是处于具体的文化内涵和实质性的价值内容的规定性当中的。如果审美背后的这种文化价值的具体性,被扩展为一个空前抽象的普遍性层面,那么,这种抽象的普遍性要么本身是一种危机的表征,要么这种抽象普遍性背后仍有着具体的价值内容和价值指涉——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下,这两种情形当然也可以共存。实际上,“日常生活审美化”它所赞美和合法化的,正是这种摆脱了任何价值重量和价值关涉的抽象的普遍性和失重的空洞性本身,是对于审美关系、价值论关系的抽象性和空洞性本身的纯粹直观和赞叹。因此,它就达到了对于日常生活的这样一种判断:“日常生活”本身已经无关于“好”与“坏”的价值判断,无关于从人性和价值本身出发的“好”与“坏”的判断。这里于是只剩下了纯粹物的标准、物的关系和物的法则,只不过它被抹去了在工业时代、机器时代的阴郁、冷漠,涂上了一层叫做“审美化”的薄薄的亮光和轻快的色泽。在这里,所谓“美的原则”就是“物的原则”。作为“需要的体系”的生活伦理和生活组织,现在纯粹经济化和物质化了,它作为经济主义的“自律性”的体系,现在变成了“自我需要”的体系:“需要”需要“需要”,“物质”消费“物质”,需要和消费本身已经失去它的生活和生存方面的根源和基础,变成一种空洞的形式和仪式化的东西。这里头确实有着物质生产丰富和某种社会生活变动等方面的因素,但却绝不是仅仅“审美化”那么无辜和值得乐观。在这里,可以看到某种比之于艰难的生存环境和赤裸裸的经济关系条件下更大的价值空洞和虚无性,一种更加接近于末世癫狂和歇斯底里式的脆弱性和危险性。
胡塞尔在20世纪早期提出“生活世界”的概念,在现象学的语境条件下,其用意一方面旨在反对科学主义、实证主义,另一方面反对历史主义、相对主义。科学主义、实证主义否定了价值问题,历史主义、相对主义主张价值问题只是相对性、临时性的问题,前者使生活成为机器,后者使生活成为碎片。胡塞尔的思路,实际上肯定了生活世界本身的价值实质性,和关于生活、价值问题本身的真理性(也即否定了历史主义和相对主义),至少是为这样一种思维路径留出了空间。作为胡塞尔的弟子,施特劳斯的问题性实际上与此内在地相关。出于施特劳斯式的政治哲学视野,任何政治活动实际都不可能离开关于“更好”或“更坏”的情况的考虑,而在权衡“更好”与“更坏”的情况时,不可能不考虑“好”或“坏”本身的问题。因此,从苏格拉底以来,政治哲学的根本问题,是对于最好政体或最好社会的探求,或者对关于最好政体或最好社会的学说的探求:“它们指向关于好或坏的知识,或更为准确地说,它们指向关于完美政治的‘好’(好的社会的本质特征)的知识。”[3]这也就是说,政治哲学不仅根本不可能离开价值问题,而且本身就是某种价值论(以及以之为前提的社会科学)的元问题。如果我们还能够对于社会生活和政治社会以目的论的方式进行一种理性化的理解和认知,那么政治哲学将永远是一种前提性和根本性的东西,政治哲学对于思想者来说,将是“一个永恒的诱惑”。
因此,“何为最好政体或最好社会?”这样的苏格拉底-施特劳斯式的问题性,本身即使没有答案,也仍然是结构我们的生活体制和政治现实的实质性力量。因为说到底,政治不是采取何种理论、何种答案的问题,而是如何去生活的问题。政治哲学是在理论与实践、观念与生活二者之间的临界面上,对此两方面关系的一种强化表达,它将此两个层面之间的关联与冲突的关系突出地展示出来。政治哲学最大程度地将“实践的哲学”和“哲学的实践”这两个层面的问题维系于一身。在这样一种问题张力中,施特劳斯将现代性的危机归之于政治哲学的危机,更赋予了这一问题以一种宏大的现代性历史批判的维度。在施特劳斯看来,现代性的根本危机就在于人们已经认定,人类不再能够理性地区分“事实”和“价值”,不再能够区分好的价值与坏的价值[4],不再能够根据自己确信的目标来理解政治社会,于是实证主义的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由此诞生。根据这样的政治思维和政治哲学,社会生活和政治组织原则不再能够凭借某种价值目标来进行规划和设定,而完全变成了一种抽象规范形式的自我参照的、实证主义的“合法性”体系。这样一种情形,无疑在现代自由主义政治那里得到了全面的实现。根据施米特的见解,鉴于自由主义、包括自由主义的政治概念和政治思维本身就是一种经济理性和经济思维的体现,经济由此最终变成人类生活的中心和最重要的东西,经济原则、经济法则和经济逻辑,终于成为生活世界和政治社会的或显在或隐蔽的根本律法。作为实证主义“社会科学”的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都只是这一切问题本身的表征和再现,根本不能寄予什么希望。在此前提下,施特劳斯于是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将现代性的危机归结为“政治哲学的危机”,这实际上赋予了政治哲学以摩西律法的地位——即使不是肯定性、正向的律法,也是一种否定性的反向律法,以此构成对于解除了任何观念和价值理念负荷的、尼采描述过的“末人”式生活方式的根本性对抗。施特劳斯的政治性,不是因为他的政治哲学的观念内容是政治性的,而最终在于他赋予政治哲学和哲学思维的这种律法力量和伦理性质。或者说,施特劳斯的“显白教诲”是哲学的,“隐微教诲”却是戒律性质的,或者说,他的“显白教诲”是疑问式-哲学式的,“隐微教诲”却是肯定式-政治式的。这不是不同部分之间或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而是不同层次的问题。施特劳斯、以及上述的施米特至少使我们明白,不仅观念的内涵,而且观念的秩序和观念的形式,会在同样、甚至是更大程度上影响生活组织和生活世界的构成。
从这样的政治哲学视野出发,我们可以将“日常生活审美化”看成是一种问题症候,那就是作为日常生活组织原则的伦理和政治法则,彻底变成了经济主义中立性的、“超功利”审美问题,价值问题以及政治理想、政治目标的问题,彻底变成了经济自律及其内部循环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在施特劳斯看来作为现代文明根本性困境和问题的东西,现在被以“审美化”的方式,优雅地加以合理化、理想化了,并且还获得了静态观照的“审美距离”:“在纯粹的审美领域,无论宗教、道德、政治的决断,还是科学的概念,都不可能有立足之地。但确实存在着这样的局面:一切重要的对立与分歧,善与恶、敌与友、基督与敌基督,都能变成审美对比,变成小说情结的手段,能够从审美角度被融入艺术作品的整体效果。”[5]只不过,这种距离是作为对于“崇高”客体——日常生活组织和生活世界——无法把握的消极形态和消极后果出现的。当人们遭遇“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时候,就像是康德哲学中的认知理性与“物自体”的关系,恰恰表明“日常生活”已经完全处于“审美关系”之外,处于我们的理性认识和实践占有能力之外。因此,这里应该做的是先考察一下我们的认知和实践能力本身出了什么问题,而不是急于赞美这个“审美化”的世界如何如何。这和认知方式和思想方法有关,但更与生活世界的实质性改变有关,从理论上不能仅仅停留在对于事实的描述上,而是到应该做出相应的改变和调整的时刻了。然而,这种理论和生存的双重失重状态,却被一部分人描述为一种“生活”世界的超升。
二、“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前世今生
对于一些人来说,“日常生活审美化”仿佛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命题,而是其中每一个字眼都像积木游戏一样可以随意地摆弄和把玩,并且总能刺激他们浮想联翩的灵感,进而从中发现了美学的“生活论转向”和“生活美学”;反过来,按照他们的逻辑,批评“日常生活审美化”,就是在批评“日常生活”,进而就是在批评“生活”本身——于是这只能让批评者无地自容。而另外一部分人也许会说,像“价值”、甚至“政治哲学”这样的概念,都是些陈旧的概念,在一个“解构主义”和“后现代”时代,探讨这样的问题未免不合时宜。这样的说法,完全没有分清问题的性质和层次:这里根本不是在探讨关于“价值”本身的概念和理论,而是在探讨现实生活和政治社会中的价值安排。从概念的意义上讲,不要说“价值”,就是“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何尝不是陈旧的概念(因此那些将它们当成时髦的东西的人才足见其不合时宜),但能否因为它们是陈旧的“概念”就不再考虑现实的价值安排等方面的问题?这就好比,能否因为“军队”是个陈旧的概念,就不再需要军队、不再需要布署军队和组织国防?连一些最基本的思想脉络和学理常识都搞不清楚,却一味地胡搅蛮缠,实在让人觉得不值得一辩。
“日常生活审美化”当然跟一种理论传统和文化传统有关,这就是认识论上的经验主义、实用主义,政治哲学和政治文化上的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消费主义的生活伦理本身,就是一种“审美”主义态度:抽象的、原子化的经济-消费“个体”和“人性”,中产阶级式的审美“超功利”、“价值中立”,力图拔除一切观念和意识形态视域的“审美距离”……康德在资本主义走向全盛的前夕,用他抽象的先验哲学体系所把握住的政治经济学内容,作为充分发展了的欧洲经济自由主义的德国理论,远远比那些纯粹英美世界中的经验主义哲学更为有力和充分,同时也对于后者有着持久的规定性影响和理论激发力量,以至于无论后者怎样花样翻新,还是逃不出康德的藩篱。这也就是说,康德美学只是对于这一切的系统化和理论化充分表述,反过来,这一切也没有颠覆康德美学的基本框架,而充其量只是其极端性的表现。或者也可以说,在自由主义-消费主义的生活伦理和生活法则中,已经具备了“审美”主义、包括“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一切原则和条件。同时,从大的思想和文化渊源上看,也就是说,追溯这个命题本身的思想文化渊源而非拘泥于这个命题出现的时限,那么它与实用主义美学一样出自同一个思想文化传统,所以它们二者之间,也很难说究竟何为因何为果。
因此,“日常生活审美化”怎么看都像是经典美学框架内的一个含混不清的局部性问题或浅层次问题,或者是一种患上了思想失忆症、残缺不全的经典美学知识。“日常生活审美化”以及对于它的一些辩护,恰恰仍然延续一种将感性和理性尖锐对立起来的80年代式的启蒙思维,因而始终认为,感性的东西是更开放、更自由的,按此逻辑,“审美化”远远比不上“动物化”和动物世界“开放”和“自由”。一个动物化的感性不值得赞美,当人们说审美的感性和自由的时候,其前提是这样的审美不仅仅是感性的,而首先是人性化的东西。从一些很古老的学术传统和学术观念,我们就知道,人性化的领地,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动物化的感性,后者恰恰被束缚和拘囚于种种低层次的局限性当中。感性的东西需要文化的、理性的东西来规定、组织和中介,把这些东西抛开,那就只剩下了物质性和动物性的感性,这样的“感性”恐怕是比之文化价值和理性领域的东西更加不自由、更加贫乏的监牢。它其实也无所谓“感性”,只是一种物质性的自在和客观性的在场,最典型的动物性在场:一种不能被中介、被反思、被观照的“感性”,只是沦陷在自在的直接性中的感性,其实也就根本无所谓丰富还是贫乏,它完全是处于这样的价值评价和价值论视域之外的。但当它们在某种被中介、反思和观照的情况下,它们也就不再是那个自在的动物性的同一性和客观性了,不再是那个消极的物质性了。而中介性和反思性的媒介和介质,更不只是那个自在的物质感性本身。所以动物化的“感性”世界没有价值领域和价值论空间,没有审美和艺术。当上述这样一种情形据说要被扩展到全部的日常生活领域时,或者说,“日常生活”领域已经被如此地加以“审美化”和感性化的改造时,我们可以想象那是一个何等令人窒息的情形。一切人性化的东西,都在其中失去了重量,这种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早已被一些现代、后现代的作家、艺术家作过艺术性的再现和批判,现在却被以“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名义正面肯定下来,并且据说还要继韦伯所谓的“理性化”之后,成为普遍性的社会组织法则。
在作为国内“日常生活审美化”观念来源之一的德国哲学家沃尔夫冈·韦尔施的著作中,曾经讲到四种“审美化”:浅表审美化、物质和社会现实的审美化、生活实践态度和道德方向的审美化和认识论的审美化。首先,将欧洲语言中兼有“感性”和“审美”双重内涵的概念完全翻译和理解为汉语中“审美”和“美学”的意义,这本身就不是很恰当。实际上,韦尔施讲述的并非是一个新问题:“不管人们喜不喜欢它,一切有思想的反对意见自身将受其支配。倘若你回溯到论争的基本点上,那么通常你就会碰到审美的选择。这是因为在现代性中,真理已经表明自身就是一个审美范畴,根植于真理之中的辩解不复能够反击审美化。”[6]作为一个后现代的美学家,这样的表述并非是一种纯粹的正面论证,我们不能用理解康德、黑格尔的哲学语言的方式理解它。之所以“一切有思想的反对意见自身将受其支配”,之所以“真理已经表明自身就是一个审美范畴”,那是因为预先就设定了真、善、美这样的古典的概念武装,但韦尔施一方面游走于“感性”和“审美”的概念内涵的张力之间,另一方面周旋于“真理”和“美学”这样的古典概念武库当中,其中明显具有后现代式的解构、反讽和话语游戏意味,以其有意制造的丰富或含混,用来表明我们当代的思想条件和认知处境。事实上,韦尔施对于四种“审美化”中的“浅表审美化”(触动当下中国学界神经的所谓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其实主要涉及的是这一层次),就是完全持批判态度的,而韦尔施最为重视的所谓的“认识论的审美化”,无非是指现实是建构出来的对象、理解现实的“生产”范畴之类。这样一些认知方式上的感性化/审美化变动,正如韦尔施自己讲到的,在尼采那里就早已得到充分的表述。但仅仅从认识论和审美的角度理解或接续尼采的现代性批判,这只是一个很狭窄的视野,甚至是一个歪曲和误读的视野。尽管他认为对于“当前的审美化既不应当不加审度就作肯定,也不应当不加审度就否定”[7],但在审美问题上保持“超功利”的中立和客观,这恰恰正是“审美主义”的态度本身,表明了“审美”意识形态的绵延和现实效用。韦尔施受阿多诺等人的影响,终究对于审美赋予了过多的乌托邦色彩[8],尽管是一种“后现代”式的乌托邦。
当我们深究“日常生活审美化”命题的时侯,会发现它其实很难被具体化,会发现它确实只是一个“原则”,一个内容上极其空洞和可疑的“原则”和单纯的意识形态叙事。“谁的审美化?”也只是对于它的一种批判方式和向度,此外还有各种批判的可能性。它的具体所指究竟是什么,其实很难究诘,它本身就是对于那种关于审美的现实规定性与文化价值内涵的空洞性和对于生活世界、生活形式无从把握的这双重空洞性的表征,以及对于“崇高”客体(生活世界、日常生活)的震惊、发呆效果本身的写照。“日常生活审美化”作为“震惊”效果,大概就是这样一种情形:像无头苍蝇似的“文化研究”,不知在哪家高楼大厦光滑的玻璃幕墙上不小心滑了一跤,然后爬起来震惊于这个世界的“审美化”。当美或者审美脱离了任何的现实规定性和文化价值内涵,它本身就变成一种纯粹形式化和空洞化的东西。就“日常生活审美化”而言,它究竟在哪些方面体现了人性化的价值和内涵?它在哪些方面更让人们感觉到身心的舒适和愉悦?当我们细加审视的时候,会发现实际的情形正好相反,它更接近于“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的审美失控状态。对于眼前这个越来越鲜亮、愈来愈“美丽”的世界,相信每个身处其中的人都有切身感受,那就是它并不是让人越来越惬意与舒适,而是令越来越多的人焦虑和狂躁,所谓的“审美化”,其实只是审美垃圾和审美污染充斥的世界。这一切当然不能都归结为审美“增量”本身的结果,但同样也说明这样简单地赞美“增量”结果也还为时过早。
美学这个概念本身带有强烈的西方哲学传统色彩和学科规训意味,就像上文所讲到的,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意图,韦尔施这样激进的理论家也不得不在附着于它之上的传统的阴影内部工作。而在西方哲学传统内部颠来倒去地进行的概念搬运,恐怕也很难说清楚究竟是颠覆了传统的稳固性,还是论证了它的强大的在场。“认识论的审美化”实际上带来了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的哲学和理论的认知和思考对象、我们生活于其间的这个世界,整体上变成了一个“审美物自体”,优雅地徘徊于我们的理论和认知能力之外,彻底消解了理论思维和认识活动的有效性。如果我们还承认人类生活还离不开哲学和理论上的认识活动,而这样的认识活动无论如何也要比审美更为基本和重要一些,我们必须将“认识论的审美化”读作强烈的反讽和讽刺。但要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需要的既不是认识论的视野,更不是美学和审美的视野,而是涉及到对于哲学和理论生活本身的正当性作出辩护的问题。这种辩护本身根本上讲不是哲学和理论的,而是政治性的——这样的对于哲学生活的政治辩护,是施特劳斯意义上的“政治哲学”的内在要求和前提条件。[9]出于这样的哲学和理论生活的正当性要求,需要的当然不是重构形而上学体系,但也不是对于“认识论的审美化”继续进行超功利的“审美”,将这样的荒诞场景变成无关利害的“小说情节”,而是需要直面哲学和理论生活背后的价值观念的政治性冲突和文化战场。
三、人究竟应该如何生活?
人能不能够不带任何观念负荷、价值观念去生活?人能不能够带着许多种价值观念去生活?至少在目前的历史条件下,“末人”式的生活方式好像还是只是另一种“观念”——“日常生活审美化”作为其朦胧和局部的预演,可以说明这一点。说取消任何价值观念本身仍是一种观念,从纯概念的层次上,这是一种概念上的无聊的还原主义和抽象拉锯,但从生活和生存的意义上讲却并非如此,而确实是对于现实情状的残酷指认和艰难表达。在这一点上,施特劳斯不仅像施米特一样,主张某种实质性的价值,而且他将这种实质性的价值赋予了具体的载体和“肉身”——“政治哲学”,来直接面对现代性的思想和理论上的敌人。施特劳斯将政治性化为思想和哲学本身的政治性,化为价值观念本身的肉身化的战斗与敌对性:
它们中的每一个都声称知道或握有真理、决定性的真理、关于正确生活之道的真理。然而真理只能有一个。这些要求之间的冲突必然也是思想存在物之间的冲突;这意味着无可避免的争论。[10]
这就将问题性高度尖锐化了,也将观念之为观念的性质挑明了。但正如不能从隐喻的意义上理解《圣经》一样,一定不能从隐喻的意义上来理解这一点,即将哲学和理论上的“政治”和“敌人”理解为实际政治的投影。在施特劳斯那里,政治哲学具有摩西律法和柏拉图哲学中的“理念”的地位,“要像柏拉图理解他自己的思想那样理解柏拉图的思想”[11],所以倒过来的理解倒更接近于真实:现实的政治倒更像是政治哲学层次上的“政治”和观念敌对性的投影。正因为现代思维总是习惯于从“隐喻”的层面上进行理解,于是一开始就把哲学理解成了“哲学”而不是一种生活方式,因此根本就理解不了价值的实质性和内在性境地,根本理解不了神圣性的东西和古代哲学。于是,在这里就展开“古今之争”的恢宏战场。
像“末人”式的不带任何价值观念去生活,带着一种价值观念去生活,乃至带着许多种价值观念去生活,同样都只是一种生活方式。人类生活从根本上讲,只能是建立在某种价值上的自我肯定基础上的同一性和统一性的生活。在这里,哲学和理论并非最重要的事情,如果它不是一种完整意义上生活方式的表征的话。因此,重要的事情不是去选择何种生活观念,而是选择何种作为生活方式的观念,选择何种观念下的生活。就像犹太人问题不可解决就是犹太人的生活方式一样,带着“何为最好政体或最好社会?”这样的问题去生活,给我们带来的并不是许多种生活方式,而是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的实质,就是承认人本身的有限性、带着人先天而来的非自足性和非完善性去生活:如果我们不知道何为最好政体或最好社会,至少我们应该保持这样的提问的问题意识,至少我们应该知道什么不是最好政体和最好社会。因此上述生活方式其实就是包含了一种“负的”或消极性的价值决断。说到底,人其实最终只能选择一种生活方式,“多元”和“多样”的生活方式的幻像,多数情况下只是同一种生活方式的具体内容和表象。“换一种活法”说说容易,实践起来何其难哉,而且其结果也不一定真的换了一种活法,而只是同一种生活方式内部的不同程度上的变动。所以,“多元主义”带给我们的并不是许多种生活方式,并不是“多种多样”、“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从根本上说,它带来的同样只是一种生活方式。
带着某种观念去生活,这种生活当然不一定是理论性和哲学化的生活方式,也不一定需要通过理智上的确认和论证再去“生活”,但一定是具有某种伦理性规范和精神性重量的生活方式。现代生活根本上的自欺性质在于拒不承认这样一种基本的事实:多数人只能也必须生活在即成的观念系统当中,多数人只能且必须依赖于某种价值理念去生活。不承认这样一种事实,却一定要自己去设想某种“观念”,自己去实现某种“价值”:就像每个人分一块糖一样,人们以为精神世界中也必定有同样多的观念之糖,可以人手一块。事实上,世界上哪有那么多的观念和价值?其实又何须那么多的观念和价值?因此人们对于“自己的”观念系统的追求和价值理念上的“自我实现”,不是空洞的,就是依附在已有的更为宏大观念和价值体系之上。于是现代人的观念生活不能不成为一种纯粹的形式和仪式,或成为一种纯粹的自我欺骗:一种形式化和仪式化的自欺,一种自欺的形式与仪式。所以不能用理解物质的方式,来理解观念世界和这种观念引导下的生活方式的“一”与“多”、单调与丰富,后者遵循的是与物质世界完全不同的秩序和规则。
就像打碎了的镜子不再是镜子,一个破碎化的观念领域,不只是带来多种多样的观念、“多元化”的观念领域,而且也改变了观念领域与生活世界的关系。观念世界的解体不是越来越精神化,而是越来越物质化,尤其是,人们已经无法辨析宏大、超越的观念性的内容,而只是以物质主义的态度面对观念。我们今天看到的是,观念世界越来越物质化,越来越获得了某种物质性的重量,这样的说法既有比喻的意义,也有非比喻的意义:这也就是说,今天这样一个挤满了物质主义世界,随时随地所分泌和剥蚀下来的一些低智商的生活观念、价值观念,不仅越来越具有物质般的微渺的坚固性,而且,观念内涵中确实也越来越充满了物质性的标准与物质性诱惑,观念领域越来越被物质主义的逻辑所主宰。它们可以轻易地虏获那些穷极无聊而又特别善于自我欺骗的心灵,它们仿佛自在自为地只是为了自身的存在而存在。过去人们直接把握观念的内容,认同观念的价值内涵,现在人们首先知道观念是一个“观念”,知道自己需要一个“观念”。然而观念的物质性重量越重,它的精神性重量越轻。人们从物质占有的逻辑出发,不可理喻地迷恋“多”而鄙弃“一”,认为“多”一定比“一”要好,“增量”一定比没有“增量”要好。数不清的“价值观念”、“价值理念”,就这样在一个离地15公分的高度上,与芸芸众生翻滚于物质主义的海洋当中。人类生活遵循着物质主义逻辑、对于观念的这种物质般的依赖性,恰恰正是现代生活的所谓“观念化”特征。人们在不同的观念之间,不是宁静地生活在观念的纯净的光照之中,而是以迷恋物质般的态度执著于自己也不知所云、辞不达意的“价值观念”。因果性在这里已经混淆不清,已经无法从理论上说明何以如此,但结果是确实如此。那些伟大的精神世界的太阳,就是这样一步步地下降到类似人造的塑料荧光棒的地步。黑格尔曾经以历史主义的姿态,揭示现代生活本身的观念化性质——但也只是历史性地揭示而已,并没有去进一步探究这种性质的根源及其背后的危机所在;尼采对于“理论人”的批判,也可以看成从另一个方向指向了这一事实。
随着观念世界的解体,因为人们已经分不清何为“观念”,人们终于达到这样一种地步,即人们根本上已经无法辨识到生活本身的肯定性和同一性、统一性。这种肯定性和同一性、统一性,本来是人们借助于观念化的东西来意识和实践的。这种观念化的东西,完全可以是前理性和前理论化的、直觉理解的东西,对于生活来说,这已经足够;只有当我们将这种观念的形式(从而也将其内容)本身置于认知和反思程序之下时,才有了理性和哲学。这种在古代哲学中曾经以本体论诘问和神圣性观念方式体现出来的实践感和存在意识,在近代哲学中或许勉强获得它的认识论和认知理性层面上的抽象对应物。在黑格尔那里,这种基础性的同一性、统一性是由意志的理性性质决定的,或不如说是由意志与理性的关系决定的。[12]但在黑格尔之后的政治哲学,根本没有能力去确证这种人类生活根基处的、肯定的同一性——也许最多是批判的同一性(如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抽象的同一性(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以及由于这种同一性的变动所带来的人类生活的质变。施米特告诉我们,后者才是政治性的根源。施米特本人不得不以一种区分性和否定性的方式,重新凝聚起这种同一性和同质性,以确保政治性之为政治性。施米特的政治的概念是一个建立区分与否定基础上的概念,但它却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强化和确立起一种更深层次上的基础性的人类生存的肯定性和同一性、同质性。因此将施米特的政治理论称之为“政治存在主义”也有一定的道理。
与施米特不同,表明温和的施特劳斯的意义实际就在于以一种更为极端、更为根本也更为坚定的问题方式,重新揭示出这种同一性:人要从根本上肯定自身,才能坚持这种基础性的同一性,才能生活,因此,这种同一性既不是源于理性也不是源于意志,它本身才是理性之源。这样的一些说法,我们看出其中的“理论”意味已经很稀薄和朴素,这恰好说明它到了理论的边缘处和开始处,或者说,正如上面的论述所显示的,这是靠近理论的开端、起源处的论证。所以施特劳斯关于文明的定义是正好说反了:文明不是有意识的理性文化[13],而是理性源于生活与生存基础上的文明和文化意识。而施特劳斯的政治性也要从这里去寻找,而不是去“隐微教诲”与“显白教诲”之间的关系中去寻找:人有没有理性都要生活,但只有肯定性的生活,才可能是好的生活;而只有好的生活,才有延续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即坚持自身的同一性和统一性。带着苏格拉底式的问题和疑问去生活,也仍然是一种肯定性的生活方式,或者不如说,更加是一种肯定性的生活方式。说到底,并没有否定性的生活方式:反抗式的生活方式,隐居遁世的生活方式,在其更深层的根基处,也都是一种生活方式,都是作为一种价值上自我肯定生活方式,来延续自身。
政治哲学视野的内在要求,实际也包括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审美”情境的内在性当中自我陶醉,而是需要一种内在与外在、“内部”和“外部”贯通的整体性视野。从“外部”视野来说,一个没有政治理念和政治远见的国家和共同体,只是一个纯粹的经济符号和经济组织的存在,只是一个他者眼中与其利害无关的或正面、或反面意义上的“审美客体”。对于某些“他者”来说,其实正是以这样的超功利的“审美”的眼光,来打量那些对于他们的生存构不成利害关系的客体、对象的,而别的国家成为这样意义上的“审美客体”,正是他们不胜欢迎的。所以,我们不能只在日常生活的内部搜寻无处不在的微观政治和文化政治,而应该有勇气为整个民族和文明共同体设立一个外部的政治理想、政治抱负和政治目标,并进而从内部重新组织我们的生活伦理和生存情调。到那时,人们才不至于把“日常生活审美化”这样不堪的历史拐角处的回光和蜃影,当成是某种生存的庆典。
注 释:
[1][3] 施特劳斯:《苏格拉底问题六讲》,《经典与解释》(刘小枫、陈少明主编)第8辑,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
[2][5] 施米特:《政治的浪漫派》,冯克利、刘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4页。
[4] 施特劳斯:《我们时代的危机》,见《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刘小枫编,彭磊、丁耘等译,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11页。
[6][7][8] 韦尔施:《重构美学》,陆扬、张岩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40、45、97页。
[9] 参见迈尔:《为什么是政治哲学?》,见迈尔《隐匿的对话——施米特与施特劳斯》,朱雁冰、汪庆华等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
[10] 施特劳斯:《哲学与神学的相互关系》,林国荣译,见迈尔《古今之争中的核心问题》一书附录,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
[11] 施特劳斯:《评科林伍德的历史哲学》,见《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刘小枫编,彭磊、丁耘等译,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155页。
[12] 参见拙文:《“后文化批评”:经济理性时代的“文化”实践》,《山花》,2010年第1期。
[13] 施特劳斯:《德意志虚无主义》,见《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刘小枫编,彭磊、丁耘等译,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117页。